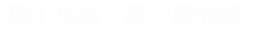【白菜与女人,同样的质朴平凡】作者:黎荔

立冬过后, 经过霜打的应季白菜上市了 。 绿白相间的白菜, 一颗颗这样肥大白硕, 包心瓷实, 心紧叶嫩 。 大叶厚实, 菜心却柔媚如花 。 抱一颗浑圆的大白菜回家, 或煮或炖或炒或凉拌, 即使是再笨拙的一位煮妇, 拿出一棵白菜, 也能做出十盘八盘的花样来 。
齐白石老先生有一幅写意的大白菜图, 画面上点缀着鲜红的辣椒, 并题句说:“牡丹为花中之王, 荔枝为百果之先, 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, 何也 。 ”是说白菜因为常见, 所以不那么被人重视, 白石老人这几句话替白菜抱不平, 说得公允 。 在北方, 一到冬天鲜菜价格嗖嗖上涨, 初冬才上市、耐贮又价廉的白菜, 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备菜 。 平民都得掐着口袋过日子, 这省那省、东拼西凑的, 怎么吃都行的平价大白菜, 是漫长寒冬的当家菜, 做法多样, 百吃不厌, 真是当之无愧的平民美食之王 。
说到白菜, 回过头来看鲁迅小说《伤逝》, 这是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 。 小说中的涓生和子君, 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, 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, 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, 最终以一“伤”一“逝”而结局 。 “只是盐和干辣椒、面粉, 半株白菜, 却集在一处了, 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 。 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, 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, 在不言中, 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。 ”这是涓生看到的“分手”之后子君所作的最后安排, 这段静物素描似的文字叙述, 读之令人动容 。 小说写得极其平常, 即便在写二人从热恋到分手的过程也未发生什么重大事件(也许失业算), 只有一些絮絮道来的家常里短, “油鸡们”和“叭儿狗”, 破屋, 板床, 半枯的槐树和紫藤, 盐和干辣椒, 面粉, 还有半株白菜……

在涓生的追忆中, 曾经, “期待子君的到来 。 在久待的焦躁中, 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, 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!”然而, 生白炉子, 煮饭, 蒸馒头, 婚后的真实生活, 建立每日“川流不息”的吃饭上 。 子君终日“汗流满面, 短发都粘在脑额上”, “倾注着全力”“日夜的操心”家务, 换来的不是丈夫对她的感谢和爱, 而是涓生对她“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”的描述 。 可涓生不可能不吃, 而子君也就不可能停止操劳 。 到涓生失业在家译书, 更加不满子君没有先前那么幽静, 善于体贴, 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, 弥漫着煤烟, 使人不能安心做事, 还有鸡狗们的烦心以及由此引发的邻里争吵 。 小家庭面临生存危机, 涓生想到的恰恰不是他所说的“携手同行”, 而是像杀掉油鸡, 甩掉小狗阿随一样地摆脱子君, 为此而费尽心机 。 贫贱夫妻百事哀, 如果不是“半株白菜”的日常家当的呈现, 又怎能烘托出涓生子君的困窘呢?数月无肉寻常事, 一年四季咬菜根 。 这“半株白菜”的贫贱蜗居之恋, 那宛转的凄伤直刺入后世读者的骨髓, 就像冬夜窗隙里的丝丝冷风 。
我想起朦胧诗人顾城和其妻谢烨, 1979年, 二人在火车上偶然结识, 一见倾心, 最终冲破种种障碍于1983年结婚 。 那时他们的生活困窘, 但依然恩爱 。 有一次, 顾城领了150元的稿费, 顾城就跟谢烨手拉着手去银行存钱, 可是下午就发现必须拿10元钱来买白菜, 两人又手拉着手去银行取了10元钱 。 后来, 他们去国离乡, 在新西兰人烟稀少的激流岛上定居, 开始了“世外桃源”的隐居生活 。 由于二人都没有正经工作, 语言又不通, 生活比在国内更加艰难, 常常吃的就是山上的植物野菜 。 1993年10月8日, 顾城在激流岛的家中和妻子发生冲突, 并用斧头砍倒了她 。 在仓皇崩溃中, 顾城随后上吊自殒 。 曾经美好的爱情和十年的姻缘, 最终以玉石俱焚的惨烈方式结束 。 这是比鲁迅小说《伤逝》中一“伤”一“逝”更为暗黑的结局 。
推荐阅读
- 【花】长寿花叶子发软下垂怎么回事 叶子变软原因与补救
- 【叶子】三角梅叶子发软下垂怎么回事 变软原因与补救
- 【栀子花】栀子花叶子发软下垂怎么回事 叶子变软原因与补救
- 【栀子花】栀子花干枝怎么办 干枝枯叶原因与处理
- 【栀子花】栀子花叶子发黑怎么办 有黑斑原因与补救
- 罗马数字78 78的含义
- 汽车知识|转速怎么算,车轮转速与车速的计算关系
- 【作用】松子的功效与作用 松子的营养价值高不高
- 【功效】洋葱的功效与作用禁忌 园葱怎么做好吃
- 【功效】安化松针茶的功效与作用 松针茶为什么不能多喝